一九○七年一月二十六日,辛約翰的《西部痞子英雄》在都柏林的艾比劇場首演,但演出內容與觀眾的期待有明顯落差。觀眾鼓譟,幾乎引起暴動,最後還動用警察維持秩序,才能繼續演下去。
二十世紀初期,愛爾蘭的民族自治運動風起雲湧。詩人葉慈有感於民族運動必須深耕於文化,因此創立艾比劇場,作為愛爾蘭文藝復興的基地,專門演出愛爾蘭戲劇。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高漲的氛圍下,劇場成為鼓舞士氣、建立純正愛爾蘭文化的重要場域。同時期,「去英國化」(de-Anglicization)的思維高漲,作家們開始重建與發明「純正」的愛爾蘭文化。但辛約翰的戲沒能完全符合這樣的期待,反而因對愛爾蘭西部農民與女子的輕蔑描述而引爆衝突。爭議的焦點在於,這齣戲是否忠實傳達了「愛爾蘭性」(Irishness)的文化價值。
辛約翰為了寫這齣戲,曾到愛爾蘭西部的愛蘭島(Arran islands)住過幾年。愛蘭島因位處外海,未受英國文化污染。據說此地保存了最純正的愛爾蘭文化。辛約翰在此採集民俗文學,親身體驗農漁民的鄉間生活。有了這樣的背景,大家對辛約翰這齣戲產生很高的期待,沒想到失望更大。從史料看來,大家對劇情的離奇與西部鄉村文化的再現最有意見。特別是劇中出現的農民愚蠢無知、道德觀低落、語言粗鄙猥褻,鄉村女子則盲目迷戀外地人。都柏林的城市人觀眾,對這樣的呈現大感震驚,這與傳統認知裡純樸善良的西部人印象截然不同。劇本的主戲是一位外地來的浪子,以華麗、詩意、夢幻的言詞炫耀自己弒父,意外引起村人對其「英雄」行徑的崇拜。特別是村女竟互相吃味競逐,以取青睞。儘管這樣的情節安排頗有驚悚效果,卻也引來觀眾的批判,大家無法接受愛爾蘭西部竟是如此一個毫無生氣、文化窒息的地方;愛爾蘭女子竟然會為殺父兇手著迷,此乃污衊善良西部民眾的不道德之舉。劇作家顯然刻意扭曲事實,存心不良,因之撻伐聲不斷。
辛約翰在接受採訪時說,他寫這齣戲的目的,與如何忠實再現愛爾蘭生活無關,他只想取悅自己。他的戲是他自己對藝術表現形式的一種追求,這個故事碰巧是彰顯此一目的的素材而已(Kilroy 23-24)。這也許是他面對龐大壓力的脫詞。仔細閱讀本劇,我們其實可以發現辛約翰別有用心,他的寫作暗地裡呼應著文藝復興的調子,表達愛爾蘭民族主義的基本訴求。觀眾雖未能體會,但他毅然為之,可謂用心良苦。
我們可以就「弒父」這個古老議題出發,來詮釋這齣戲的可能意義。本劇裡主人翁克里斯帝用鋤頭劈父親老馬宏,然後逃到愛爾蘭西部去避災。這個弒父情節可視作殖民的隱喻,是愛爾蘭人反壓迫、追求獨立自由之舉。劇中的父子關係,可以從政治文化、語言更新的角度來探討。愛爾蘭從十二世紀以來就受英國殖民,喬伊斯就說,愛爾蘭人是「一僕二主」,愛爾蘭這個僕人在政治上有個英國主人,在宗教上則有個義大利主人 (Joyce 638)。愛爾蘭人在生活裡飽受英國殖民壓迫,同時也在精神信仰上受制於羅馬天主教。因為殖民統治,英國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全面滲透到愛爾蘭人民的生活與行為裡。一九○七年,本劇發表的同年,英國成立優生學研究學會,透過學術機構的建制力量,統治者把愛爾蘭人描繪成缺少文化的野蠻民族,酗酒、情緒化、喜喧鬧的次等人類,必須接受英國的父權統治領導。有識的愛爾蘭民族主義人士起而抗之,辛約翰是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 (Irish Revival)健將之一,他的創作巧妙把喬伊斯主僕式英愛關係,轉化成更強烈的父子關係,並加以顛覆。
劇中的克里斯帝與老馬宏這對父子,父親瞧不起兒子,說他「滿口胡言,愚蠢至極」,說他無能懶惰,幾乎一無是處。戲開場時,克里斯帝狼狽出場,他在壕溝旁「像瘋狗一般狂吠」,「看起來快死了」,是個「鬼鬼祟祟的傢伙」,又冷又餓,像隻被追逐的野獸,掙扎著到酒館裡靠在火爐邊取暖,乞討酒喝(30, 35)。酒館主人去參加守靈,克里斯帝在此遇到店主女兒佩珍,展開一段浪漫戀情。克里斯帝說自己的父親脾氣暴躁,令人難於忍受,「一旦他睡著,打呼聲總是鎮天大響。只要他醒來以後一定大發雷霆,就像低俗的官員破口大罵三字經」。他的兒女成群,但「他們只要在深夜裡咳嗽或打個噴嚏醒來,總是大聲咒罵父親」(48-49)。父親的形象竟是如此,所以克里斯帝殺父所展現的勇氣,反而贏得西部愛爾蘭人民的欽佩,進而成了眾人仰慕的大英雄。辛約翰把英愛殖民的「父子」 關係轉換到馬宏父子上(劇中從未提及克里斯帝的母親,只說有個奶媽帶他),他解構這些虛構的父子關係,透過委婉的殖民隱喻,賦予弒父正當性。但在劇末,辛約翰倒置父子的權力關係。克里斯帝在西部參與當地人的日常生活,舌燦蓮花重塑自己的形象,參與村人競賽贏得勝利,成為人人吹捧的英雄,創造了自己的傳奇。猶如成長小說的原型,克里斯帝經過殺父逃亡,最後在西部重生,以成熟獨立的男子漢重回故里。最後一幕父子和解,克里斯帝已非昔日吳下阿蒙,他自信昂揚,竟對老父發號司令,逆轉了過去的權力關係。許多的評論家如Steve Wilson等,都以克里斯帝的成長蛻變為主調詮釋本劇。
但這樣二元對立的解讀,恐怕過於簡化。辛約翰畢竟是一流的劇作家,他在結局裡留下反諷的空間。如同評論家Nicholas Crawford所說,劇本的結局是兩個團圓。克里斯帝與老父團圓,一起重回故里。而佩珍恐怕只能和她瞧不起的熊凱歐結婚,留在西部鄉下單調沈寂地渡過一生(492)。兩個結局都指向悲觀的現實,文藝復興的努力,若沒能從精神上改造愛爾蘭人民,則一切都是徒勞無功,只能回到過去麻木的舊生活。如果克里斯帝真正地蛻變成長,他也許該離開故鄉,出去打拼自己的天下,而不是隨著老父回到鄉下繼續苟活;如果佩珍受到感召,她可以勇敢離家去逐夢。可惜兩人都回到沈寂不變的傳統現實裡。辛約翰似乎在暗示,愛爾蘭民族主義所企盼的人民覺醒,以當時的情況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辛約翰進一步把父子關係延伸到宗教上去。本劇中有兩對父子:一對是馬宏父子,一對是雷利神父與熊凱歐。這兩對父子,某種程度反映了兩種愛爾蘭子民的認同意識。克里斯帝因為反抗父權暴力,勇敢殺父,反而在愛爾蘭西部特殊的地理人文環境中得到救贖,獲得自我實踐的成長,蛻變為全新的愛爾蘭青年。反觀熊凱歐屈服於雷利神父的威權,唯唯諾諾,不敢有絲毫反抗之意。雷利神父從未出場,但他的「不在場」反而彰顯了天主教對愛爾蘭人民的影響無所不在。熊凱歐追求佩珍,為取得雷利神父的應許,對他百依百順。但佩珍瞧不起他的膽怯懦弱,反而仰慕克里斯帝,她希望嫁給像他這樣有文采、有膽識、有行動力的青年,而不是熊凱歐這種信仰盲目、麻痺而不自知的庸俗愚人。愛爾蘭人民在英國殖民統治下,有些人起而抵抗,有些人則在殖民與宗教的洗腦與軟性監控下認同錯亂,失去了自主意識。
克里斯帝從一位逃亡的流浪漢,後來成為眾人追捧的對象,主要來自他說故事的能力。辛約翰這齣戲除了劇情離奇,成功吸引觀眾注意外,劇中豐富生動且多變的語言表現也功不可沒。劇中克里斯帝隨著逐漸融入梅尤地區的生活,語言表現也越來越鮮活生動。佩珍為他侃侃而談的風采著迷,他的語言充滿浪漫詩意、動人心弦。例如第三幕克里斯帝對佩珍說:「我們可以散步到艾瑞斯。到時候你就可以聽到我的呢喃。喝一小口井水,再用濕潤的嘴唇狂吻……到時候要是主教看到你,我想,他們一定會像神聖的預言家一樣,從天庭欄杆處爭相目睹特洛伊海倫的風采」。佩珍就承認說,「任何女子要是遇到像你這麼會花言巧語的年輕人,鐵定要掏心掏肺……你不但有詩人的口才,還有顆勇敢的心」(96)。 一位鄉村農夫的兒子變得口才便給,克里斯帝就像劇作家本人文采非凡。語言表現改變了克里斯帝,語言成了肯定自我、建構認同的重要因子。
認同問題也是一種語言問題。凡受到外來殖民統治的人民,本土語言必然受到壓抑,愛爾蘭也不例外。愛爾蘭文藝復興伴隨著恢復母語的主張,語言問題成了認同問題的延伸。但這齣戲的語言並非標準英語,也不是純正的梅尤地區方言,而是辛約翰式的雜化語言(Crawford 483)。他到西部地區體驗鄉民生活,但要他像在地鄉民一樣地思考感受事物,恐怕也不見得容易,畢竟他骨子裡是個英國裔的愛爾蘭人。他的語言夾雜著英語與蓋爾語的表現方式,而雜化 (hybridity) 正是後殖民語言的特色之一。辛約翰以雜化的手段來發明或重新定義愛爾蘭的認同,並透過克里斯帝這個角色來完成這個構想。作家一面以象徵父親的英語創作,一面又想辦法顛覆這個父親形象,不斷以本土語言介入英語的表達,企圖在模擬與顛覆的雙重空間裡,創造屬於自己獨特的語言與新的文學。這種蓋爾語化的英語(Gaelicized English)呼應了葉慈的語言主張:國家文學可以是一種具有愛爾蘭精神的英語書寫。這種“English in language; Irish in spirit”的說法,適度修正了海德博士「去英國化」的主張 (Kiberd 155)。克里斯帝以雜化鮮活的語言,敘述他殺父的經過,贏得西部人民的喜愛。辛約翰的寫作融合愛爾蘭的神話傳說,加上自己對英文的掌握能力,以獨創的雜化語彙豐富了愛爾蘭文學的表現模式。辛約翰的語言實驗,「謀殺」了英語的正統權威,結合在地語言,成就了自己獨特的劇場美學(Crawford 495)。
辛約翰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而走向西部鄉間,他在尋找不受英國污染的純正本土文化之際,也發現了西部真實的一面。十九世紀中葉,因馬鈴薯欠收而起的大飢荒,連帶引發移民海外的浪潮,鄉村裡有能力的人都遠走海外,尋找新的生活機會。西部鄉村急速沒落,人民生活了無生趣,文化情境幾乎奄奄一息。死亡氛圍濃厚,就像劇中大量出現的孤兒、酒鬼、威權的神父、愚昧的信徒、失落的父親、弒夫殺子的寡婦,在在反映一個道德淪喪、價值錯亂的西部。這個真實的面目,與多數在都市裡高喊自治的民族主義人士對西部的認知大相逕庭。反諷的是,辛約翰的劇本「忠實」呈現這樣的西部,反而被批為蓄意污衊純樸的愛爾蘭文化。
面對過度美化的西部概念,辛約翰並未跟著盲目歌頌,反而採取據實以對的態度,忠實呈現他所感受到的西部。不扮喜鵲,喜作烏鴉,他希望以藝術的手法診斷生病的愛爾蘭文化。這有點像喬伊斯,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,批判都柏林人的麻痺心理,面對殖民統治卻不能真正從心底自省自覺。
克里斯帝的西部流浪記戳破了這個神話,辛約翰所描繪的克里斯帝,並非文藝復興人士所期待的,代表正統高尚的愛爾蘭文化。克里斯帝並非完美的「英雄」,他兼具兩面性格,一方面懦弱,同時又勇敢;有時浪漫,有時凶殘;一面屈從,一面又抗拒;有時輕率,有時又認真,是個充滿矛盾的凡人。某種程度上,克里斯帝象徵愛爾蘭文化的多元矛盾面貌。愛爾蘭並非單一民族,而是包含諾曼人、西班牙人、維京人及凱爾特的傳統,還有盎格魯撒克遜人。在追求國家獨立與文化認同的同時,民族主義人士必須正視愛爾蘭文化的多元性,否則一味偏執,將帶來更大的族群對立,釀成國家無法融合的災難,恐非好事。
辛約翰反思文藝復興的路線,他不完全認同葉慈美化凱爾特神話及西部農村純樸的想像。他所創造的痞子英雄克里斯帝,比現實的西部民眾更具有生命活力。痞子精神是叛逆、反威權、具行動力、想像力豐富、言語趣味,這才是愛爾蘭最欠缺也最需要的。這個劇本「忠實」地彰顯了這個痞子精神的迫切性。
弔詭的是,這部當年飽受批判的戲,今日竟是艾比劇場裡非常受歡迎的經典劇碼。今日重讀此劇,它的藝術價值早已超越當年的風風雨雨。
最後,這個劇本是由專事愛爾蘭文學研究的年輕學者張崇旂執筆翻譯。本劇最大的特色之一,就是它特殊的語言實驗。融合正統英文與愛爾蘭西部在地的表達方式,翻譯難度相當高,但張崇旂的譯文忠實流暢、可讀性高,是親近愛爾蘭文學不可或缺的譯本,值得大家細細品味。
參考書目
Crawford, Nicholas. “Synge’s Playboy and the Eugenics of Language.” Modern Drama, 51.4 (Winter 2008): 482-500.
Joyce, James. Ulysses. New York: Vintage, 1986.
Kiberd, Declan. Inventing Ireland. London: Vintage, 1986.
Kilroy, James. The Playboy Riot. Oxford: Oxford UP, 1971.
Wilson, Steve. “His Native Homespuns… Become Him”: Synge’s 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Performative Identity.” Midwest Quarterly, 48.2 (2007):233-246.
※ 本文同步刊登於莊坤良部落格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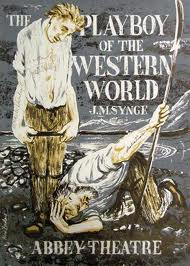

No Comments Yet